上海青帮的覆亡:揭秘上海青帮三大亨的悲喜命运
字号:小号|大号
推荐阅读
本周热门
- 三国司马懿简介?历史上司马懿是怎么死的呢?
- 汉武帝的四位皇后分别是谁 他们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故事?
- 刘备是怎么死的?三国演义中的遗憾刘备之死
- 古代最抢手的女人:母仪天下命带桃花的萧皇后
- 曹操死后谁继位 曹操去世后由哪个儿子继位?
- 太平天国运动 太平天国洪秀全死后军事行动
- 曹植在兄弟中排行老几?历史上曹植是怎么死的
【内容导读】帮会和黑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是历代当权者所面对的一个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清王朝无法解决帮会问题,民国政府也解决不了黑社会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同样也面临着如何解决帮…
帮会和黑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是历代当权者所面对的一个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清王朝无法解决帮会问题,民国政府也解决不了黑社会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同样也面临着如何解决帮会和黑社会这个社会性难题。
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政府是代表劳动人民利益的,认为帮会和黑社会的一般成员,原本也是下层社会的穷苦人民,由于他们的基本利益和生存权利的不得保障,才被迫铤而走险,走上和主流社会相悖离或对立的道路;即使是上海黑社会的青帮三大亨,也都是穷苦出身。因此,要解决帮会和黑社会问题,必须从解决底层社会劳动人民的生存问题入手。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立了工会、农会等劳动者的组织,帮助广大穷苦百姓解决就业和生活问题。帮会以往那种互助和抗暴的功能已经失去了作用,帮会的组织也就不再有存在的理由,因此人民政府便命令帮会和黑社会自行解散,对于有罪恶的帮会头子则予以惩处;对于一般帮会成员,则帮助他们解决生计问题,使之重新回到劳动人民当中。一般的帮会和黑社会的头子失去了群众基础,成了光杆司令,也就无法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相抗衡,只好接受改造,重新做人,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至于上海青帮三大亨,由于各自的原因,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得到了不同的结局。
一 黄金荣:悔过却难自新
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占领南京,结束了国民党政权,陈毅率领的第三野战军准备进驻上海。4月27日,杜月笙、王晓籁、金廷荪等人已经前往香港,黄金荣究竟何去何从?他面临着十分矛盾的心情。他明白他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无疑是个有罪的人:他在四一二事变当中,曾积极参加反革命活动,屠杀了不少共产党人;后来自己又为法国租界当局服务了多年,是外国帝国主义的走狗;在充当青帮头子的几十年当中,干了大量欺压百姓和危害社会的事,成为上海黑社会的龙头老大。因此担心如果留在上海,共产党肯定饶不了自己。当时很多人劝他前往香港,但他担心身体吃不消,他说:“我的年纪已经80多岁了,死在香港倒不要紧,只怕路上生了急病,岂不要死在半途!”又对心腹说:“杨虎讲,共产党的领袖知道我,可以既往不咎,并且写了条子,由杨虎转交给我,我可以在解放后交给上海的负责人,不会捉我。”这样,黄金荣最后还是下决心留在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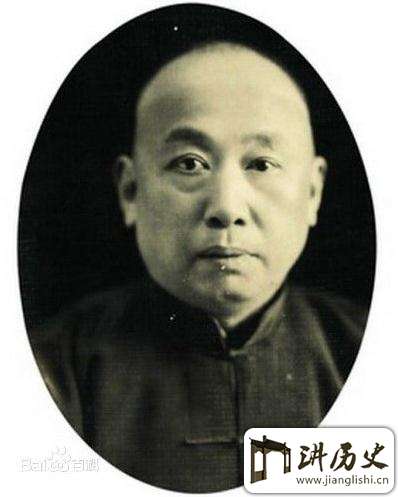
不过,他还是做了两手准备:一方面决定不参加国民党撤离前的大搜捕、大屠杀,掩护一些地下党员,支持他们接管上海,并且让门生搜集帮会头目的情报,将一份400名帮会头目的名单交给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以便对其进行控制,防止他们进行捣乱;又让管家黄振世将他知道的国民党财产加以登记,请杨虎转交给地下党;他还告诫弟子不要参与国民党逃离前的破坏活动。另一方面他则让儿媳李志清把他所有的金银、外汇等财宝带往香港。尽管黄金荣自称他对李志清携带钱财前往香港一事并不知情,但从后来的许多事表明,这乃是黄金荣的另外一手准备。李志清在香港不仅汇钱给他,而且还按照他的指示,在香港、澳门购买了房产,甚至还拍了照片,在照片后面写好姓名、年龄、籍贯和住址,并让李志清在香港为他申请了去台湾的入境证。
上海解放初期,黄金荣照常经营他的产业,如大世界、黄金大戏院、荣金大戏院等,每月都有一笔不菲的收入。黄金大戏院出租给华东文化部下属的大众剧团,每月收入约数百万元(旧币)。黄金荣还有几处房产,也都由门徒承包,对外出租,租金数目可观。黄金荣在生活上也没有太大的变化,鸦片照抽,澡堂照泡。解放初期人民政府之所以没有对他加以惩处,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领导人就已经对帮会组织有过明确方针,即只要他们不出来捣乱,不干扰上海解放后的社会治安,老实接受改造,就不动他们。特别是对于黄金荣、杜月笙这样的帮会头面人物,采取“观察一个时期再说”的方针,目的是“努力使上海不乱”。上海市长陈毅和分管政法工作的副市长潘汉年,认为黄没有逃走,没有破坏,说明他至少对中共不抱敌意。他现在不问外事,就不必把他当做专政对象,只要他表示态度就行。所以,解放初期一直没有动黄金荣。1951年年初,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后,黄金荣的日子开始难过起来。一封封控诉信、检举信,递向上海市政府和公安机关,恳请政府对黄金荣加以处理。在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下,人民政府开始着手处理黄金荣的问题。上海市人民政府委派盛丕华、梅达君、方行三为代表,出面召见黄金荣,向他说明既往政策不变,但希望他能写“悔过书”公开登报,老实认罪。黄金荣让龚天健执笔,写了一份自白书,1951年5月20日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全文如下:
我小时候,在私塾读书,十七岁到城隍庙姊夫开的裱画店里学生意,二十岁满师,在南门城内一家裱画店做生意,五年后考进前法租界巡捕房做包打听。那时候,觉得做裱画司务没出息,做包打听有出息。现在想来,做包打听,成为我罪恶生活的开始。
我被派到大自鸣钟巡捕房做事,那年我二十六岁,后升探长,到五十岁时升督察长,六十岁退休,这长长的三十四年,我是一直在执行法帝国主义的命令,成为法帝国主义的工具,来统治压迫人民。譬如说卖烟土,开设赌台,危害了多少人民,而我不去设法阻止,反而从中取利,实在真不应该。
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政府是代表劳动人民利益的,认为帮会和黑社会的一般成员,原本也是下层社会的穷苦人民,由于他们的基本利益和生存权利的不得保障,才被迫铤而走险,走上和主流社会相悖离或对立的道路;即使是上海黑社会的青帮三大亨,也都是穷苦出身。因此,要解决帮会和黑社会问题,必须从解决底层社会劳动人民的生存问题入手。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立了工会、农会等劳动者的组织,帮助广大穷苦百姓解决就业和生活问题。帮会以往那种互助和抗暴的功能已经失去了作用,帮会的组织也就不再有存在的理由,因此人民政府便命令帮会和黑社会自行解散,对于有罪恶的帮会头子则予以惩处;对于一般帮会成员,则帮助他们解决生计问题,使之重新回到劳动人民当中。一般的帮会和黑社会的头子失去了群众基础,成了光杆司令,也就无法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相抗衡,只好接受改造,重新做人,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至于上海青帮三大亨,由于各自的原因,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得到了不同的结局。
一 黄金荣:悔过却难自新
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占领南京,结束了国民党政权,陈毅率领的第三野战军准备进驻上海。4月27日,杜月笙、王晓籁、金廷荪等人已经前往香港,黄金荣究竟何去何从?他面临着十分矛盾的心情。他明白他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无疑是个有罪的人:他在四一二事变当中,曾积极参加反革命活动,屠杀了不少共产党人;后来自己又为法国租界当局服务了多年,是外国帝国主义的走狗;在充当青帮头子的几十年当中,干了大量欺压百姓和危害社会的事,成为上海黑社会的龙头老大。因此担心如果留在上海,共产党肯定饶不了自己。当时很多人劝他前往香港,但他担心身体吃不消,他说:“我的年纪已经80多岁了,死在香港倒不要紧,只怕路上生了急病,岂不要死在半途!”又对心腹说:“杨虎讲,共产党的领袖知道我,可以既往不咎,并且写了条子,由杨虎转交给我,我可以在解放后交给上海的负责人,不会捉我。”这样,黄金荣最后还是下决心留在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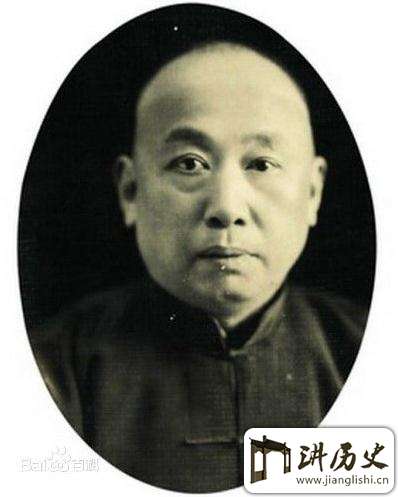
不过,他还是做了两手准备:一方面决定不参加国民党撤离前的大搜捕、大屠杀,掩护一些地下党员,支持他们接管上海,并且让门生搜集帮会头目的情报,将一份400名帮会头目的名单交给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以便对其进行控制,防止他们进行捣乱;又让管家黄振世将他知道的国民党财产加以登记,请杨虎转交给地下党;他还告诫弟子不要参与国民党逃离前的破坏活动。另一方面他则让儿媳李志清把他所有的金银、外汇等财宝带往香港。尽管黄金荣自称他对李志清携带钱财前往香港一事并不知情,但从后来的许多事表明,这乃是黄金荣的另外一手准备。李志清在香港不仅汇钱给他,而且还按照他的指示,在香港、澳门购买了房产,甚至还拍了照片,在照片后面写好姓名、年龄、籍贯和住址,并让李志清在香港为他申请了去台湾的入境证。
上海解放初期,黄金荣照常经营他的产业,如大世界、黄金大戏院、荣金大戏院等,每月都有一笔不菲的收入。黄金大戏院出租给华东文化部下属的大众剧团,每月收入约数百万元(旧币)。黄金荣还有几处房产,也都由门徒承包,对外出租,租金数目可观。黄金荣在生活上也没有太大的变化,鸦片照抽,澡堂照泡。解放初期人民政府之所以没有对他加以惩处,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领导人就已经对帮会组织有过明确方针,即只要他们不出来捣乱,不干扰上海解放后的社会治安,老实接受改造,就不动他们。特别是对于黄金荣、杜月笙这样的帮会头面人物,采取“观察一个时期再说”的方针,目的是“努力使上海不乱”。上海市长陈毅和分管政法工作的副市长潘汉年,认为黄没有逃走,没有破坏,说明他至少对中共不抱敌意。他现在不问外事,就不必把他当做专政对象,只要他表示态度就行。所以,解放初期一直没有动黄金荣。1951年年初,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后,黄金荣的日子开始难过起来。一封封控诉信、检举信,递向上海市政府和公安机关,恳请政府对黄金荣加以处理。在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下,人民政府开始着手处理黄金荣的问题。上海市人民政府委派盛丕华、梅达君、方行三为代表,出面召见黄金荣,向他说明既往政策不变,但希望他能写“悔过书”公开登报,老实认罪。黄金荣让龚天健执笔,写了一份自白书,1951年5月20日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全文如下:
我小时候,在私塾读书,十七岁到城隍庙姊夫开的裱画店里学生意,二十岁满师,在南门城内一家裱画店做生意,五年后考进前法租界巡捕房做包打听。那时候,觉得做裱画司务没出息,做包打听有出息。现在想来,做包打听,成为我罪恶生活的开始。
我被派到大自鸣钟巡捕房做事,那年我二十六岁,后升探长,到五十岁时升督察长,六十岁退休,这长长的三十四年,我是一直在执行法帝国主义的命令,成为法帝国主义的工具,来统治压迫人民。譬如说卖烟土,开设赌台,危害了多少人民,而我不去设法阻止,反而从中取利,实在真不应该。
历史解密战史风云野史秘闻风云人物文史百科
左良玉在明末为什么能手握百万雄兵?
左良玉是明朝将领,多次与农民起义军征战,到了后来他拥兵百万,成为南明朝廷最重要的倚仗。这位将领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对于他...详情>>
看亚美尼亚特种兵如何玩命:生食兔肉脚上点火!
亚美尼亚特种兵在武装部队情报局成立纪念仪式上,表演生吃活兔、头顶碎大石、刀扎肚皮、脚上点火……精彩与彪悍程度令人乍舌。相...详情>>
水浒传里花和尚鲁智深为什么说他最后成了佛?
征方腊会老,梁山众将十去七八,战死者、病死者不在少数,那么作为梁山108将中,最为光彩照人的好汉鲁智深,他的归宿在何处呢?为...详情>>
王安石严于律己:从未包二奶 一生无任何绯闻
北宋是一个重文轻武的朝代,文官的地位很高。在当时的京城开封,许多国家公务员追求享乐和奢侈的生活,娶小老婆和包“二奶”的国...详情>>
吴禄贞一生是怎样的?吴禄贞一生都做过哪些事?
吴禄贞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家有薄田10亩,父亲为私塾老师。少年时,吴禄贞就读于父亲在武昌的梦泽书屋,他擅长诗文,对西学充...详情>>



 2016日本AV女优排行榜 最受欢迎5大女优出炉
2016日本AV女优排行榜 最受欢迎5大女优出炉 激情男女路灯下上演活春宫 大爷一旁淡定围观
激情男女路灯下上演活春宫 大爷一旁淡定围观 蟒蛇大战食人鳄:谁才是水中霸王?
蟒蛇大战食人鳄:谁才是水中霸王? 揭秘朝鲜土豪生活 KTV夜总会一样都不少
揭秘朝鲜土豪生活 KTV夜总会一样都不少 揭秘:人头蛇身怪物的真相之谜
揭秘:人头蛇身怪物的真相之谜 男子与母女同床 竟同时使两人怀孕
男子与母女同床 竟同时使两人怀孕 男子当众表演“把头塞进鳄鱼嘴巴” 没想到悲剧就在下一秒发生
男子当众表演“把头塞进鳄鱼嘴巴” 没想到悲剧就在下一秒发生 毒蛇挑衅二斤重蜈蚣王,反被啃得只剩下脊骨
毒蛇挑衅二斤重蜈蚣王,反被啃得只剩下脊骨 雄狮活吃野牛,开膛破肚肠子外露,胆小者慎入!
雄狮活吃野牛,开膛破肚肠子外露,胆小者慎入! 怀孕小三商场内遭暴打 内裤都被扯断了
怀孕小三商场内遭暴打 内裤都被扯断了 红卫兵大串联
红卫兵大串联 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候的华国锋
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候的华国锋 古埃及罕见木乃伊,尸体保存完整,身份大有来头
古埃及罕见木乃伊,尸体保存完整,身份大有来头 老照片:9·11中恐惧的白宫高官
老照片:9·11中恐惧的白宫高官 老照片:全球核武器爆炸解禁照片曝光
老照片:全球核武器爆炸解禁照片曝光 老照片:1945年日本投降十大经典画面
老照片:1945年日本投降十大经典画面 老照片:史上最著名的20幅造假照片曝光
老照片:史上最著名的20幅造假照片曝光 老照片:披露希特勒自杀现场
老照片:披露希特勒自杀现场 历史罕见瞬间
历史罕见瞬间 美国空军历史上的悲剧时刻
美国空军历史上的悲剧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