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历史上名士调侃司马相如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字号:小号|大号
本周热门
- 南明弘光帝有多荒淫:当众将幼女演员强奸致死
- 揭秘:历史上刘邦为何对老实厚道的大哥耿耿于怀
- 惊:史上竟然有吃美女的习俗
- 梁山好汉五大好色之徒:宋江竟榜上有名
- 宋朝是365足球投注上最繁华 百姓最幸福的朝代吗?
- 司马懿之妻张春华为何亲手杀人!司马懿老婆是谁
- 古龙笔下最精彩的15部小说及十大枭雄介绍
【内容导读】读《世说新语》,发现作者经常借时人之口调侃司马相如。比如,在《任诞》里有这样的叙述:王孝伯(王恭)问王大:“阮籍何如司马相如?”王大曰:“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
读《世说新语》,发现作者经常借时人之口调侃司马相如。比如,在《任诞》里有这样的叙述:王孝伯(王恭)问王大:“阮籍何如司马相如?”王大曰:“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刘孝标注云:“言阮皆同相如,而饮酒异耳。”类似的叙述大概出现了三次。仔细分析,确然事出有因:魏晋那一帮林下诸贤,虽然和司马相如一样,都相当能闹腾,但在骨子里或许是真的瞧不起司马相如。
将两汉的文人墨客都从棺材里揪出来晒晒,也就司马相如一人,可以和魏晋的古惑仔们有得一拼。于是,司马相如可能非常不幸地成了魏晋名士们的“出气筒”。司马相如玩过著名的私奔,这在儒家子弟的眼里,属于“恣情任性”和“倜傥放荡”的不检点行为。而在魏晋名士们的眼里,此举纯属小儿科。阮籍的做法是,居丧期间勾引邻家美貌少妇,且是有夫之妇,简直惊世骇俗,分明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还一下子成了时尚达人(《晋书》评曰:达而无检)。此类事例甚多,人所熟知,不待详引。
司马相如不但嗜酒如命,还自己酿过酒,当过酒馆的店小二,这叫什么?叫“嗜酒荒放”。可是,魏晋名士们对此依然嗤之以鼻,他们认为,司马相如嗜酒,只是寻常的“杯中之好”罢了,说句不好听的,就是贪杯,他心中没有须酒浇释的“垒块”。这种情绪在后人的诸多注释中多有出现,比如鲁迅先生就曾揭示过。而竹林七贤的嗜酒,其背后有着政治高压下的穷途末路之心态,醉酒,是他们最后的安身立命之所。司马相如有过在宫殿里脱裤子撒尿的“劣迹”,还被廷尉抓了现行,告以大不敬之罪,算起来也是潇洒裸一回了。可是,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澄就是不买账,他以实际行动予以反击:当着一帮子文武百官的面,全裸爬树抓喜鹊(解衵脱衣上树、裸形扪鹊),还跟市井卖帽子的老婆婆调笑,甚至直呼父亲的字。

司马相如的“劣迹”,饱读诗书的王澄不可能不知道。比较一下可以发现,前者是偷偷摸摸,后者是光明正大,前者是“宵小之行”,后者是公然结交宵小,前者是袒露身体,后者不光袒露,还对父亲构成大不敬。变本加厉至极,近乎不耻了。难怪当时的“士庶莫不倾慕之”。司马相如再怎么闹腾,汉武帝始终也没严办他。以刘彻数十年执行刑罚之酷(独尊儒术是面子功夫),司马相如能仅以身免,说明了什么?后人将其归于弄臣之列,赵炎以为,恐非空穴来风。弄臣之弄,即玩弄之弄也,说白了,你司马相如不过是刘彻的开心果而已,没怎么把你当盘菜。那么,这一点,司马相如自己知道吗?完全明了。据史载,他常说笑话逗刘彻开心,奴才之面孔昭然若揭。有一顶帽子叫气节有亏,给司马相如戴,尺码恰好合适。
再看魏晋诸名士,无论在朝在野,皆是朝廷的反对派和对立面,抵触与不合作,是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气节一条而言,他们瞧不起司马相如的理由,已经足够了。另外,姓氏上的渊源,或许也构成了魏晋名士对司马相如的排斥。虽然司马相如是成都人,而司马懿是河南温县人,八竿子扯不到一块儿。但是,打断骨头连着筋,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即周宣王执政时期官拜司马(管辖军政和征战的官职)的程伯休父(《通志·氏族略》)。因此,司马氏主政的朝廷对司马相如其人其文推崇备至,而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名士群体极力调侃司马相如,借以讥讽当局和当局的奴才们,就存在可能了。历朝历代,有才的奴与有才的人之间的斗争,莫外如斯。
将两汉的文人墨客都从棺材里揪出来晒晒,也就司马相如一人,可以和魏晋的古惑仔们有得一拼。于是,司马相如可能非常不幸地成了魏晋名士们的“出气筒”。司马相如玩过著名的私奔,这在儒家子弟的眼里,属于“恣情任性”和“倜傥放荡”的不检点行为。而在魏晋名士们的眼里,此举纯属小儿科。阮籍的做法是,居丧期间勾引邻家美貌少妇,且是有夫之妇,简直惊世骇俗,分明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还一下子成了时尚达人(《晋书》评曰:达而无检)。此类事例甚多,人所熟知,不待详引。
司马相如不但嗜酒如命,还自己酿过酒,当过酒馆的店小二,这叫什么?叫“嗜酒荒放”。可是,魏晋名士们对此依然嗤之以鼻,他们认为,司马相如嗜酒,只是寻常的“杯中之好”罢了,说句不好听的,就是贪杯,他心中没有须酒浇释的“垒块”。这种情绪在后人的诸多注释中多有出现,比如鲁迅先生就曾揭示过。而竹林七贤的嗜酒,其背后有着政治高压下的穷途末路之心态,醉酒,是他们最后的安身立命之所。司马相如有过在宫殿里脱裤子撒尿的“劣迹”,还被廷尉抓了现行,告以大不敬之罪,算起来也是潇洒裸一回了。可是,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澄就是不买账,他以实际行动予以反击:当着一帮子文武百官的面,全裸爬树抓喜鹊(解衵脱衣上树、裸形扪鹊),还跟市井卖帽子的老婆婆调笑,甚至直呼父亲的字。

司马相如的“劣迹”,饱读诗书的王澄不可能不知道。比较一下可以发现,前者是偷偷摸摸,后者是光明正大,前者是“宵小之行”,后者是公然结交宵小,前者是袒露身体,后者不光袒露,还对父亲构成大不敬。变本加厉至极,近乎不耻了。难怪当时的“士庶莫不倾慕之”。司马相如再怎么闹腾,汉武帝始终也没严办他。以刘彻数十年执行刑罚之酷(独尊儒术是面子功夫),司马相如能仅以身免,说明了什么?后人将其归于弄臣之列,赵炎以为,恐非空穴来风。弄臣之弄,即玩弄之弄也,说白了,你司马相如不过是刘彻的开心果而已,没怎么把你当盘菜。那么,这一点,司马相如自己知道吗?完全明了。据史载,他常说笑话逗刘彻开心,奴才之面孔昭然若揭。有一顶帽子叫气节有亏,给司马相如戴,尺码恰好合适。
再看魏晋诸名士,无论在朝在野,皆是朝廷的反对派和对立面,抵触与不合作,是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气节一条而言,他们瞧不起司马相如的理由,已经足够了。另外,姓氏上的渊源,或许也构成了魏晋名士对司马相如的排斥。虽然司马相如是成都人,而司马懿是河南温县人,八竿子扯不到一块儿。但是,打断骨头连着筋,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即周宣王执政时期官拜司马(管辖军政和征战的官职)的程伯休父(《通志·氏族略》)。因此,司马氏主政的朝廷对司马相如其人其文推崇备至,而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名士群体极力调侃司马相如,借以讥讽当局和当局的奴才们,就存在可能了。历朝历代,有才的奴与有才的人之间的斗争,莫外如斯。
历史解密战史风云野史秘闻风云人物文史百科
左良玉在明末为什么能手握百万雄兵?
左良玉是明朝将领,多次与农民起义军征战,到了后来他拥兵百万,成为南明朝廷最重要的倚仗。这位将领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对于他...详情>>
看亚美尼亚特种兵如何玩命:生食兔肉脚上点火!
亚美尼亚特种兵在武装部队情报局成立纪念仪式上,表演生吃活兔、头顶碎大石、刀扎肚皮、脚上点火……精彩与彪悍程度令人乍舌。相...详情>>
水浒传里花和尚鲁智深为什么说他最后成了佛?
征方腊会老,梁山众将十去七八,战死者、病死者不在少数,那么作为梁山108将中,最为光彩照人的好汉鲁智深,他的归宿在何处呢?为...详情>>
王安石严于律己:从未包二奶 一生无任何绯闻
北宋是一个重文轻武的朝代,文官的地位很高。在当时的京城开封,许多国家公务员追求享乐和奢侈的生活,娶小老婆和包“二奶”的国...详情>>
吴禄贞一生是怎样的?吴禄贞一生都做过哪些事?
吴禄贞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家有薄田10亩,父亲为私塾老师。少年时,吴禄贞就读于父亲在武昌的梦泽书屋,他擅长诗文,对西学充...详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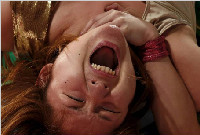

 蟒蛇大战食人鳄:谁才是水中霸王?
蟒蛇大战食人鳄:谁才是水中霸王? 揭秘不堪入目的地下影棚:女模被捆绑 任人处置
揭秘不堪入目的地下影棚:女模被捆绑 任人处置 驻日美军玩弄日本美女 场面不堪入目
驻日美军玩弄日本美女 场面不堪入目 水牛目睹雄狮配种画面 反应让人看傻眼
水牛目睹雄狮配种画面 反应让人看傻眼 湖水被倒猪血变“血湖” 引来300只吃人鳄鱼
湖水被倒猪血变“血湖” 引来300只吃人鳄鱼 职业捞尸人揭悚人经历:黄河水下直面尸王
职业捞尸人揭悚人经历:黄河水下直面尸王 主播直播中遇女鬼当场开撕 结果竟是...
主播直播中遇女鬼当场开撕 结果竟是... 辣妹报案 警察因这原因在镜头前公然“袭胸”
辣妹报案 警察因这原因在镜头前公然“袭胸” 实拍泰国“生猛”人妖秀 太豪放吓跑男观众
实拍泰国“生猛”人妖秀 太豪放吓跑男观众 27岁男子10年睡了2500个妹子 1天4个!
27岁男子10年睡了2500个妹子 1天4个! 鬼子进村扫荡真实镜头
鬼子进村扫荡真实镜头 二战日本女明星慰问日军
二战日本女明星慰问日军 1950年台湾国军演习训练旧照
1950年台湾国军演习训练旧照 1942年美国空军空袭日本东京
1942年美国空军空袭日本东京 旧照片中的真实侵华日军
旧照片中的真实侵华日军 1941年二战日本偷袭珍珠港照片
1941年二战日本偷袭珍珠港照片 诺曼底战役中各国军队的惨状
诺曼底战役中各国军队的惨状 二战时期美军虐俘照片
二战时期美军虐俘照片 饥饿与暴力:震撼心灵的非洲!!
饥饿与暴力:震撼心灵的非洲!! “夜间摄影之鼻祖”布拉塞名作
“夜间摄影之鼻祖”布拉塞名作